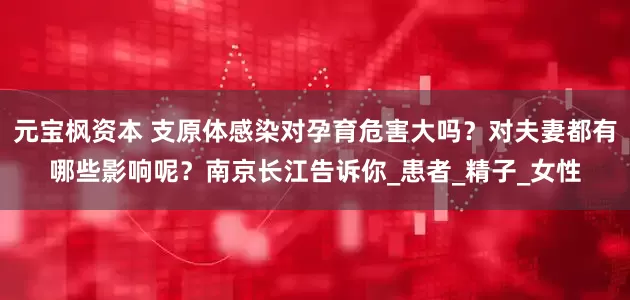日期:2025-04-22 17:38:02

引文融创配资
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近期两次重磅表态引发政经界震荡。在货币政策层面,他明确警示前总统特朗普力推的关税政策可能引发持续性通胀压力,强调"通胀回落至2%目标将比预期更久",并以此为由排除近期降息可能性。此番鹰派立场直接触发资本市场恐慌情绪,道琼斯指数单日跌幅超过500点。
值得关注的是,在回应外界对其职务稳定性的质疑时,鲍威尔展现出罕见强硬姿态。他援引《联邦储备法》相关条款强调:"无论是白宫还是最高法院,都无权单方面解除美联储主席职务。作为向国会负责的独立机构,解除我的职位需要获得参众两院三分之二议员支持。" 这种制度性防火墙的设计,正是美联储独立于行政体系的核心保障。
面对鲍威尔的"制度性宣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Truth Social"的回应堪称激烈。这位总统不仅发起"是否支持解散美联储"的民意投票,更连续发布多条动态指责鲍威尔"政策滞后且充满错误",要求立即启动解职程序。双方对峙态势将货币政策决策权与行政权力的边界争议推向白热化。
鲍威尔敢于直面总统压力的底气,根植于美国独特的央行治理架构。根据1913年《联邦储备法案》,美联储主席虽由总统提名,但一经参议院确认即获得法定独立性,其四年任期与总统选举周期刻意错开。历史上从未有美联储主席因政策分歧遭解职,这种制度设计保障了货币政策免受短期政治干扰。即便面对特朗普的激烈施压,鲍威尔仍能依托法律护城河坚守政策立场。
1. 美联储的职能与独立性
美联储作为美国的中央银行,由12家区域性联邦储备银行组成,旨在平衡联邦政府与私人银行的利益。其核心职能是通过货币政策管理美元信用,实现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历史上,政府倾向于过度印钞,而私人银行则追求高杠杆,这两者都可能损害货币信用。因此,美联储既要防范经济危机中的流动性短缺,扮演“最后贷款人”角色,又要在日常运作中以通胀率和失业率作为政策依据,维护经济稳定。
鲍威尔此次强调美联储对国会负责,且其职位受法律保护,表明他致力于维护美联储的独立性,不受行政部门的直接干预。这一立场在面对川普的关税政策及其潜在经济影响时尤为关键。
2. 鲍威尔对通胀的警惕与川普关税政策融创配资
川普政府推行的关税政策,特别是对华加征高额关税,被认为可能推高美国国内物价,引发通胀压力。鲍威尔明确表示,美联储需防备这一风险,并认为通胀可能长期存在,因此不会降息。这一决定与市场对降息的期待相悖,导致美股大跌。
降息通常用于刺激经济增长,但若通胀风险上升,降息可能加剧物价上涨,形成恶性循环。鲍威尔选择维持利率不变,显示出他对通胀的高度敏感。这与他过去的经历不无关系——2021年,美联储对通胀初期反应迟缓,导致市场对其误判通胀能力的批评,直到2022年加息后通胀回落,其声誉才有所恢复。此次鲍威尔对关税引发的通胀风险保持警惕,或是对此前教训的反思。
3. 川普关税政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川普的关税政策旨在保护美国本土产业,但其效果和代价引发争议。以对华关税为例,政策初衷是通过加征关税迫使中国承担成本,从而刺激美国国内生产。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在关税加征初期(10%-20%),美国采购商成功要求中国供货商降价,后者为保住市场份额部分让步。然而,当关税提高至54%甚至更高时,中国供货商因无法承受亏损而拒绝进一步降价,美国采购商则面临成本上升的压力,最终部分选择弃货。这一过程表明,关税成本并未完全转嫁至中国,而是部分传导至美国国内市场,推高了物价,增加了通胀风险。
对于美国经济而言,关税政策短期内可能刺激就业,但长期看,通胀压力可能削弱消费者购买力,并增加企业运营成本。鲍威尔作为美联储主席,必须通过货币政策应对这一局面。不降息的决定正是为了避免通胀失控,维护经济稳定,尽管这与川普政府刺激经济的期望相左。
4. 鲍威尔的立场与政治前景
尽管鲍威尔由川普提名担任美联储主席,但他在面对川普的压力时愈发强硬。他曾公开表示不受白宫干预,且在回应川普的“语言霸凌”时态度坚定。鲍威尔的第二任期将于2026年结束,且无法连任,这使其更倾向于秉持美联储的独立性,而非迎合短期政治需求。历史上,美联储主席往往希望在任期内留下积极遗产,鲍威尔也不例外,其强硬姿态或意在维护自身声誉。
此外,鲍威尔在拜登任期内与民主党政府合作较为密切。市场认为,美联储曾为支持经济增长而延迟加息,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民主党政策。然而,这也导致其在通胀问题上的误判,招致批评。未来,鲍威尔卸任后可能寻求其他政治或经济职位,如财政部长,尤其若民主党在2029年后重掌白宫,他与民主党的“情分”或为其铺路。然而,这将取决于当时的政治格局。
5. 结论
当鲍威尔以法律盾牌抵御总统压力时,这场看似突发性的政经博弈实则揭开了美国百年制度设计的深层肌理。从经济治理层面审视,美联储拒绝为关税政策"兜底"的决策,本质上是对政治经济周期理论的现实应用——通过锚定通胀预期阻断"贸易保护→物价上涨→货币宽松→资产泡沫"的恶性传导链条。这种反周期调控策略,与上世纪80年代沃尔克抗击通胀时的政策哲学一脉相承,彰显央行超越选举周期的战略定力。
在制度架构层面,美国刻意构建的"双重独立"机制(独立于行政体系、独立于金融市场)在此次危机中展现出设计智慧。总统提名权与国会监督权的制衡、14年理事任期与4年主席任期的错配、12家地区联储的分散决策机制,共同编织成抵御政治干预的制度网络。这种精巧的权力制衡设计,恰恰源于1935年银行法改革时立法者预见的"民选总统与专业央行"的永恒张力。
从历史坐标系观察,当前冲突实则是1987年格林斯潘拒绝为里根减税买单、2012年伯南克顶住奥巴马连任压力维持紧缩政策的现代重演。每次博弈都在强化一个基本共识:当白宫以政治逻辑推行产业政策时,美联储必须作为"制度刹车"存在。这种动态平衡机制,本质上构成了美国经济治理体系的纠错冗余。
对于现代国家治理而言,此事件提供了关键启示:央行的独立性不在于完全隔绝政治影响,而在于建立制度化的缓冲地带。通过法律赋权、人事保障、决策透明三重机制,确保技术官僚能在选举狂热与民粹浪潮中坚守专业判断。这种"受约束的独立性",恰是防止经济决策被短期民粹绑架的核心保障。
在全球化退潮与强人政治崛起的时代背景下,鲍威尔的强硬姿态超越了个人决策范畴,成为维护现代央行制度存续的关键战役。其成败不仅关乎美国经济周期走向,更将影响全球央行体系的治理范式——当主要经济体央行相继面临政治化风险时,美联储能否守住独立性底线,某种程度上决定着21世纪全球经济治理的基准坐标。
码字不易融创配资,点个关注呗!
景盛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